

四月初的陜北,高原雄峙,大河奔涌,春意盎然,生機勃勃,恰逢清明,帶著孩子回鄉祭祖,順路游覽神往已久的鳳凰山。古代文人春天的時候最喜歡干三件事,登高、燒香與看海,身居內陸,平常偶爾能看一看河也是奢望,如果能把三件事都攢在一起干了,也不失為一件雅事。
鳳凰山坐落在神木南部萬鎮強家峁村,山頭向南傾出,如展翅欲飛的鳳凰,延伸至黃河邊上,山上建有廟宇,唐代于半山腰開鑿石窟兩座,內有藻井和造像。相傳有鳳凰落于此山,我倒是更傾向于是褐馬雞落在了山頭,畢竟此處離山西龐泉溝并不遠,生態環境還未惡化的時候,有土生土長的褐馬雞也未可知。
黃土高原缺水,能生長在一條大河邊上,日子過的就不會饑荒。黃河順著晉陜大峽谷而下,兩岸高山林立,怪石嶙峋,常年的風吹日曬雨淋,很多崖壁上被雕琢出如同天書般的文字。天災、水災與人禍千百年來循環往復,人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長大,心里總要有信仰才能活下去。黃河神木市段從北至南依次建有西津寺、天臺山、娘娘廟、鳳凰山等遠近聞名的廟宇群,小點的不知名的龍王廟、關公廟、佛殿、觀音廟等散落在各個村落,敬神畏天的風氣由此可見一斑。
我小時候生長的村落在黃土高原腹地,離黃河邊大概有四十多里山路,每年的三月三鳳凰山廟會,十里八鄉的農人聚集而來,趕會聽戲,買賣交易,好不熱鬧,父輩們聊起鳳凰山趕會總有說不完的話題。鳳凰山趕會唱戲,唱的是晉劇和二人轉,這個劇種流行于陜北、內蒙古中部和山西北部,鳳凰山的戲臺建在半山腰處,坐南朝北,戲唱給山上供奉的娘娘、玉皇、天王等一眾神仙聽,農人們沾著神仙的光,聽聽戲,見見老鄉,買點日雜用品,一來一回幾十里山路也不覺得有多遠有多累。
我們沿著路牌的指引驅車上到戲臺前的小廣場,下車后抬頭就看到了數百個臺階自下而上直插天際,兒子看著高聳的臺階就犯怵,我鼓勵他戰勝恐懼,一鼓作氣征服它,兒子在前,我護在后邊,拾階而上,越往上走,臺階越陡,臨近山門處的臺階近乎垂直的九十度,兒子抓著欄桿一步一步向上挪,臺階的正中央長了一棵臭椿樹,光禿禿地沒有一點葉子,春的氣息并沒有喚醒它,爬過最驚險的那幾十個臺階,就到達了山門處。轉身遠眺,緩緩流淌的黃河就在腳下,河面寬闊,河水清澈,泛著淡淡的綠光。兩岸群山對立,溝壑萬千,青松翠柏點綴在光禿禿的石林間,沿黃公路如同一條絲帶蜿蜒纏繞在山腰處,山風和鳴,天地壯闊。
穿山門而過,沿階而上,東西各修一亭,東邊亭下掛大鐘一口,西亭置大鼓一面,兒子用木棍隨意地敲打著,鐘聲清脆,我拿過木棍教兒子橫著用撞擊的方式撞鐘,鐘聲變換,厚重悠長,響徹云霄。再往上爬就到了山頂的平緩處,正殿祖師廟和玉皇閣南北排列,香爐中有未燃盡的線香,兒子一進一出,走馬觀花地看完了兩個廟宇,順著廟后的臺階一路向北,穿后山門而出,來到了供游人休息的廊亭里坐了下來。
下午的日頭正好,我和愛人坐在石頭上,曬著暖洋洋的春日,兒子撿拾大小不一的石塊,一個一個的扔向西邊的山溝里,暖風依依,春日遲遲。面前的黃河水日夜不停地流淌,一刻也不曾停歇,山間的草木年復一年地生長,見證了無數燒香拜神的游客,黃土地上人一代代老去,口口相傳著屬于這座山的故事。
我登了高,進了廟,望了河,集齊了丐版古代文人“三雅好”,算得美事一樁。在山上待到日頭開始西下,帶著妻兒沿著盤山公路步行而下,驅車從沿黃公路往回趕,路過西豆峪村,兒子喊著要到黃河邊上耍水,靠邊停車,步行至黃河邊。從鳳凰山上望黃河,水面如鏡,聽不到一點點的水聲,一到黃河邊上,看到的和聽到的是另一番景象,河面上波濤陣陣,發出如歌如泣的嗚咽聲。年少不知山高水長,歲月靜好,如今已過不惑之年,再登山看河,聽風沐雨,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返程路上,車堵得一塌糊涂,心里卻無比的敞亮,我摯愛著黃河邊上的黃土地,山也罷,土也罷,樹也罷,草也罷,人也罷,誰怕?一蓑煙雨任平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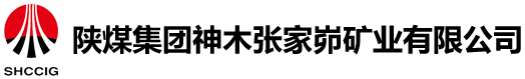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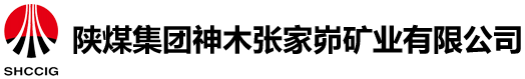

 發布日期:2024-04-12
發布日期:2024-04-12
 點擊量:1367 作者:劉波 來源:
點擊量:1367 作者:劉波 來源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