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說創作中至關重要的環節,《紅樓夢》(以下簡稱《紅》)里這一點表現的更加鮮明。這部小說不僅僅是賈、王、史、薛四家的興衰成敗經歷,亦絕非賈黛愛情悲劇那樣簡單,它里面隱藏著更多的深層次的內涵和寓意。因此,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某一個支點上去對待一部成功而又偉大的作品。我們應該放寬文學的審美視界,去探索隱匿在文學素材中更加有深度和現實意義的東西。
我們知道,雪芹撰寫《紅》的初衷并不是為了名世,他更多的是想通過作品揭示現實社會的本質。《紅》里塑造了多位女性形象,作者從神情外貌,性格特征、語言行為、歸宿命運等方面去寫女性,筆觸細膩入微,語言暢達而又明練,對一些女配角的描寫雖寥寥幾筆,卻也生動形象,極為傳神。毋庸置疑,作者把這些女性搬進文學的房間旨在為作品增色,但更多的是想贊揚女性,通過這些細節展示女性之美。
總體上來講,雪芹對“金陵十二釵”的描寫更為詳盡。對黛玉的描寫是“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,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。態生兩魘之愁,嬌襲一身之病;淚光點點,嬌喘微微;嫻靜時如嬌花照水,行動處似弱柳扶風……”。至于寶釵,除了“臉若銀盆,眼如水杏”之外,大約就是會使寶玉欣賞羨慕的“雪白一段酥臂”。王熙鳳的出場采用先聲奪人的方法,“一雙丹鳳三角眼,兩彎柳葉吊梢眉。身量窈窕,體格風騷。粉面含春威不露,丹唇未啟笑先聞”便是對其的完美詮釋。寫香菱,只寫到她那一顆胭脂;寫鴛鴦,只寫到她臉上的碎麻子;寫司棋,會寫到她的“高大身材”;寫晴雯,我們記得她有點“水蛇腰”;寫迎、探、惜三春,也只說過,“肌膚微豐,合中身材”、“削肩細腰,長挑身材”、“身量未足,形容尚小”等話語,只有對史湘云的描寫涉及到身材曲線,那便是“蜂腰猿背,鶴勢螂形”。作者在女主角黛玉身上花了不少筆墨,但外表、神情的描寫也只能歸結于“靈”,對其他女性的描寫則有“肉”的意味在其中,可見二者在本質上有“靈”、“肉”之別。
工藝品在陳列進房間之前是要經過雕琢的,精雕細琢、筆刀輕重之間都突顯著作者深刻的用意。雪芹這樣安排女性的描寫及塑造,其實已經為她們的命運歸宿做好伏筆。脂硯齋評《石頭記》時有“千紅一窟,萬艷同杯”之吟詠,《老殘游記》的作者劉鐵云對奇茗“千紅一窟”和異酒“萬艷同杯”的理解為:“……《離騷》為屈大夫之哭泣,《莊子》為蒙叟之哭泣……李后主以詞哭,八大山人以畫哭;王實甫寄哭泣于《西廂》,曹雪芹寄哭泣于《紅樓夢》;曹之言曰:滿紙荒唐言,一把辛酸淚……名其茶曰“千紅一窟”,名其酒曰“萬艷同杯”者:千紅一哭,萬艷同悲也!……“一步行來錯,回頭已百年。古今風月鑒,多少泣黃泉”是可卿的歸宿,“寒塘渡鶴影,冷月葬花魂”是黛玉苦難的慘局,“春夢隨去散,飛花逐水流”是寶釵的命定。可見雪芹也相當同情女性的命運,他是流著血,泣著淚用哀婉傷懷的文字為她們殉葬的。
在封建社會里,女性的地位是低下的。她們受著封建思想和綱常倫理道德等許多條框的限制,毫無人身自由和平等權利可言。道德倫理的包袱和思想意識的愚昧堆積起來,毫無保留地壓在她們身上,讓她們喘不過氣來,也看不到光明。盡管作者筆下的女性生活在一個大家庭里,但是她們也難以成為社會的寵愛者,最終還是成為封建社會的罹難者,跌進黯淡失色的深淵里。女性的名字,一些實物的稱謂,女性們的活動(如黛玉葬花,諸艷畢集于大觀園)等許多環節在草蛇灰線,伏脈千里間影射著女性的命運。雪芹筆下的“落紅成陣,花落水流紅”便是她們命運的真實寫照。先前迎春之嫁,晴雯之死,司棋之逐,寶釵之遷已經給女性的命運蒙上太多的無奈,凄楚、傷痛和絕望,接下去探春遠嫁,黛玉的自沉,襲人的遭遣,小紅的婚配,五兒的慘局,惜春的出家,妙玉的落難無疑讓雪芹的傷痛到了極致,也讓女性的命運、歸宿雪上加霜,這樣逐層推進在文學上來說是一種升華,同時也意味著封建政權的沒落和衰亡。
雖然生活在封建社會的女性逃脫不了命運的魔爪,可是她們身上還是洋溢著一種我們沒有發現的美。雪芹用自己熾熱的筆將它書寫的淋漓盡致,窺探了女性的心靈軌跡,憐憫她們的命運歸宿。其情之深,義之切流露在字里行間。閑余之時,手捧一杯香茗翻閱《紅樓夢》,頓覺女性之美閃耀著光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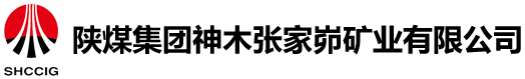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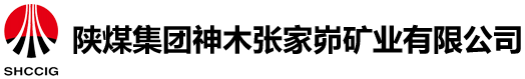

 發布日期:2021-03-12
發布日期:2021-03-12
 點擊量:1698 作者:王永耀 來源:
點擊量:1698 作者:王永耀 來源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