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“媽媽,你知道嗎?月亮還叫玉盤。”
晚飯后,女兒突然冒出這么一句。她剛滿四歲,上幼兒園中班,說話時眼睛亮晶晶的,像在說一個非常神秘的話題。我順著她肉乎乎的小手指向天空,那輪月亮確實圓潤、光潔,溫潤地浸在深藍天幕里,邊緣微微泛著青光,真像一塊被時光打磨得極好的玉。
“是李老師教的。”她得意地補充,小腦袋仰得高高的,小臉上滿是“我知道一個了不起的詞”的驕傲。
我忽然有些恍惚。“玉盤”這個詞,從她稚嫩的嗓音里流淌出來,竟如此新鮮又古老。讓我想到那首詩,“小時不識月,呼作白玉盤”,但那時朗朗上口的是音節,并不是真懂何為“玉”,更不解那清輝萬里背后,一代代人凝望的、共同的鄉愁。
而她呢?她的小腦袋瓜里,“玉盤”大概就是個新學會的、好聽的詞,和“滑梯”“彩虹糖”并列,是她探索這個世界的又一塊小拼圖。她還不明白,這個詞承載了千年月光。
這讓我想起她第一次對“中秋”有概念,是去年。
那時她三歲多,我們指著天上越來越圓的月亮,告訴她:“快中秋節啦,可以吃月餅,看月亮。”她似懂非懂,也許只記住了“月餅”是甜甜的、圓圓的點心。今年,她到底大了一些。幼兒園里做了燈籠,讀了繪本,講了嫦娥奔月的故事,還用彩筆涂了可愛的玉兔,那些古老的故事,就這么借著顏料和紙張,悄悄印在了她心里。
這或許就是節日的意義,它像一條隱秘的河流,我們帶著下一代涉水而過,將古老的傳說、共同的記憶,以及那份對團圓的樸素信仰,小心翼翼地渡給他們。
看著她專注望月的側臉,我忽然意識到,我正親眼見證著文化最初的模樣,是如何在一個純凈的生命里扎根的。它不是課本上需要背誦的詩句,也不是儀式里必須遵守的規矩,而就是這樣一個尋常的夜晚,一個新鮮的詞語,一份對遙遠故事的好奇,和一種想要與月亮分享甜食的天然親近。
我們這代人總感慨年味淡了、節味變了,仿佛那些熱鬧的儀式一散,傳統就跟著淡了。可此刻看著女兒,我忽然懂了:節日從未真正改變,它只是換了一種更質樸的方式,在下一代身上悄然延續。它藏在孩子學會的一個新詞里,藏在她對古老傳說的一絲共情里,更藏在她依舊愿意仰頭看月亮的那份專注里。
是啊,無論時代如何翻涌,科技如何狂奔,只要某個秋天的夜晚,依然有孩子指著天空說“月亮像玉盤”,只要那份仰望星空的初心不曾泯滅,那輪照過李白、照過蘇軾,照過無數代人團圓與別離的月亮,就永遠年輕,永遠溫潤如玉。
原來中秋的圓滿,從來不止于此刻家人圍坐的溫暖。更在于我們確信,這縷皎潔的月光,會帶著“玉盤”的故事、嫦娥的傳說、團圓的期盼,這樣溫柔地、穩穩地,一代一代照拂下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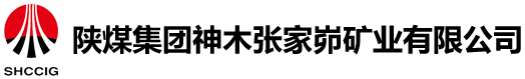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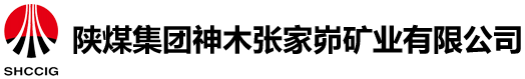

 發布日期:2025-10-03
發布日期:2025-10-03
 點擊量:412 作者:賈艷 來源:
點擊量:412 作者:賈艷 來源: